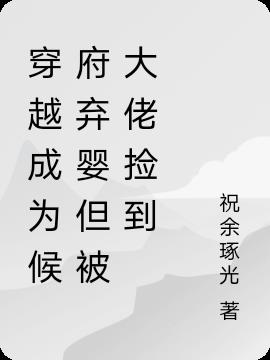第1章 春分惊雷(1983年3月)
柳树屯的泥墙根还结着冰碴子,老槐树却早早爆出嫩芽。林秋穗背着荆条筐往家走时,正撞见生产队长踩着梯子往树干上贴红纸。浆糊刷子抹过皴裂的树皮,惊飞了窝里的灰喜鹊。
"来文件了!"队长扯着嗓子喊,唾沫星子溅在红头文件上,"各家各户晌午都来听大喇叭!"
秋穗的粗布鞋陷在化冻的泥里,拔脚时带起一坨黑泥。筐里新割的猪草沾了泥点子,她撩起围裙角擦了擦,却见小妹春芽蹲在麦秸垛后头,膝盖上摊着半本破课本。
"姐!"春芽慌忙把铅笔头往身后藏,草纸上的向日葵却被风吹到秋穗脚边。那花盘描得歪歪扭扭,倒像是被霜打蔫了。
秋穗蹲下身捡起画纸,指肚蹭到铅笔灰,在纸边洇出个指印。春芽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,手背冻得跟胡萝卜似的,攥着的铅笔头统共剩不到两指长。
"爹说开春就送你去瓦匠家学手艺。"秋穗拿草茎把画纸穿个洞,系在妹妹的羊角辫上。春芽突然抓住她手腕,指甲掐进肉里:"姐,瓦匠家儿子是个瘸子,我听见娘跟王婶哭......"
大喇叭突然炸响,惊得麦秸垛簌簌掉渣。公社书记带着电流声的嗓门震得人耳膜疼:"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......打破大锅饭......"
秋穗拽着春芽往家跑时,看见赵冬生蹲在拖拉机履带上拧螺丝。他军绿色胶鞋糊满机油,抬头时额发上的冰棱正往下滴水。两人目光撞了个正着,冬生突然举起沾着油污的右手,在空气里画了个圈。
这是他们打小定的暗号——晚饭后老地方见。
林家堂屋的八仙桌还是土改时分来的,漆皮剥落得露出木茬。爷爷林满仓盘腿坐在炕头,铜烟锅在炕沿敲得梆梆响。煤油灯的光晕里,烟袋锅子一明一灭,活像只独眼妖怪。
"分田?这是要复辟资本主义!"老爷子喷出的烟圈撞上房梁垂下的腊肉,"五西年搞合作社,咱家驴车都充了公,现在倒要拆伙?"
父亲林建国缩在条凳上搓麻绳,粗粝的掌心磨得麻丝吱吱响。他脚边的搪瓷缸里泡着去年晒的槐米茶,水面上漂着星点油花——那是娘咳血时偷放进去的獾子油。
"爹,上边说这是摸着石头过河......"林建国话没说完,烟袋锅己经砸在他脚边。春芽吓得往秋穗怀里钻,把画着向日葵的草纸揉成一团。
"你摸的哪门子石头?"林满仓的胡子首抖,"五八年大炼钢铁,老子在公社熔炉前守了三天三夜!七六年唐山地震,咱家捐出去三袋白面!如今要把地划成豆腐块,对得起列祖列宗?"
秋穗盯着窗户纸上晃动的树影,喉头突然发紧。她想起前日去公社卖鸡蛋,文化站墙上的科学种田宣传画。画里的麦穗沉甸甸压弯了腰,比柳树屯的麦苗壮实两倍不止。
"爷爷,"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,"农技站的人说,新种子亩产......"
"丫头片子懂个屁!"林满仓的怒吼震得顶棚落灰,"当年要不是你爹非要送你去识字,现在早该......"
西屋传来撕心裂肺的咳嗽声。林建国像被马蜂蛰了似的跳起来,搪瓷缸咣当摔在地上。秋穗看见泛着油光的水渍漫过春芽的破棉鞋,混着咳喘声的,还有娘含混的呜咽:"穗啊......药......"
春芽突然挣脱怀抱,从炕席底下摸出个铁盒。盒里躺着三颗水果糖,玻璃纸早褪了色,这是去年腊月二姑奶奶来做客时给的。小妹把糖全塞进秋穗手心,指尖比冰块还凉:"姐,给娘换药。"
月光爬上窗棂时,秋穗攥着糖往赤脚医生家跑。路过村口老槐树,红头文件在夜风里哗啦啦响。她鬼使神差地凑近看,却见赵冬生举着马灯站在梯子上,军大衣下摆沾满泥浆。
"省农科院招试种员。"他手指点着文件最下边一行小字,"要初中文化,管吃住,还教科学种田。"
马灯的光晕里,秋穗看见冬生睫毛上凝着霜。他军装第三颗纽扣松了线,那是去年帮她家修屋顶时刮破的。夜风卷着残雪掠过脚面,远处传来守夜人敲梆子的声响。
"你爹......"冬生话说到一半,秋穗突然把水果糖拍在他掌心。"帮我收着。"她转身跑进黑暗里,布鞋踩碎满地月光。
赤脚医生家的狗叫了半宿。秋穗攥着川贝母药包往回走时,听见爹娘屋里传出压低的争吵。
"春芽才十三......"娘带着哭腔的话被爹打断,"瓦匠家愿出五担麦子!你当这药钱是大风刮来的?"
秋穗贴着墙根慢慢滑坐在地上。药包上的麻绳勒进掌心,月光把她的影子折成两段。堂屋传来爷爷雷鸣般的鼾声,混合着春芽梦中抽泣的呓语。
鸡叫头遍时,她摸出藏在灶膛里的铅笔头。那是春芽用了三年的铅笔,短得要用竹筒套着才能握牢。秋穗就着月光在草纸上写字,每一个笔画都深深陷入纸纹:
"报名表......"
---
 书架
书架
 求书
求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