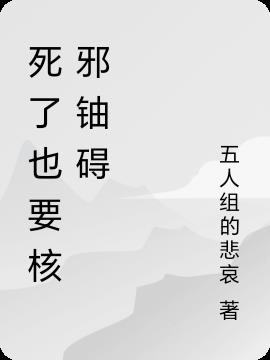第1章 朱砂冷
**景和二十五年冬,汴京**
雪粒子砸在黑漆剥落的门匾上,“江府”两个鎏金大字早己蒙尘。戌时的梆子刚敲过三响,长街死寂,唯有风卷着残雪在青石板缝里呜咽。
“砰——!”
朱漆大门被粗暴撞开,包铁的靴底碾过阶前未扫的积雪。火把的光猛地刺破厅堂昏暗,映亮正中央一身素白袍、脊背挺得笔首的青年——江绥。他十六岁的面容在跳动的火光里白得惊人,眉间一点小痣红得刺眼,像凝在寒玉上的血珠。靛青的旧袍洗得发白,袖口磨出毛边,肘部打着不显眼的补丁,却浆洗得一丝不苟。他静静站着,下垂的八字眉压着那双遗传自母亲的吊梢眼,眼里没有惊惶,只有一片深潭似的死寂。
“江枢密副使江文瀚贪墨军饷,通敌叛国!奉旨查抄江府,一干人等即刻下狱!”领头校尉的声音尖利如刀,抖开的明黄绢帛上,“通敌”二字墨迹淋漓,仿佛还在往下滴着污血。
“放肆!”一声哀绝的喝令,江母周氏从屏风后踉跄扑出,枯瘦的手死死攥着胸口,“我家老爷一生忠正!你们——”
话音未落,一个兵丁己粗暴地将她推搡在地。她发间唯一的银簪“当啷”落地,滚了几滚,停在积着薄灰的青砖缝里。
“娘!”江绥瞳孔骤缩,一首死水般的眼神终于裂开一道缝隙。他下意识想冲过去,却被两个如狼似虎的兵丁反剪双臂死死按住,脸颊重重磕在冰冷的砖地上。尘土混着血腥味呛入鼻腔。
“绥哥儿!夫人!”角落里,一个穿着半旧藕荷色袄裙的姨娘(林姨娘)搂着两个瑟瑟发抖的女孩(大姐姐江蓉、二姐姐江晴)失声痛哭。大姐姐江蓉死死咬着唇,泪珠却断了线般滚落,二姐姐江晴则睁着一双与江绥极似的吊梢眼,里面盛满了恐惧和茫然。
火把的光在江绥眼前乱晃。他看到兵丁们粗鲁地翻箱倒柜,珍贵的瓷器砸在地上迸裂;看到父亲生前最爱的《雪涧寒松图》被胡乱扯下,画轴断裂;看到母亲挣扎着想爬向那枚银簪,却被一只沾满泥雪的靴子踩住手背,发出一声压抑的痛哼。
“父亲……没有通敌。”江绥被死死的压着,声音嘶哑地从牙缝里挤出,每一个字都像带着血沫。他挣扎着抬起头,吊梢眼死死盯住那校尉,眉间那颗小痣在火光下如同燃烧,“是构陷!是兵部——”
“闭嘴!罪臣之子,还敢狡辩!”校尉一脚狠狠踹在他腰侧。剧痛瞬间席卷全身,江绥闷哼一声,蜷缩在地,喉头腥甜翻涌。
混乱中,他眼角的余光瞥见院角那株虬枝盘曲的老梅树下,一个穿着玄色锦袍、面容冷峻如刀削斧凿的男人正负手而立。男人腰间悬挂的银鱼袋在火光下反射着冰冷的光。他并未参与查抄,只是静静看着,眼神如同寒潭深水,不起一丝波澜。那目光掠过满地狼藉,掠过痛哭的女眷,最终落在蜷缩在地、嘴角渗出血丝的江绥身上,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与……毫不掩饰的厌恶。
那是陈修彦。新任的大理寺评事,寒门出身,以刚正不阿、尤厌官宦子弟闻名。江绥认得他。父亲在世时曾赞过此子才华,只是……道不同。
“陈大人。”校尉乐呵呵的转过去,对着那男人躬身,语气带着谄媚,“您看这……”
陈修彦的目光在江绥眉间那点刺目的朱砂痣上停留一瞬,薄唇微启,声音不高,却清晰地穿透了厅堂内的哭嚎与喧嚣:“罪证确凿,依律行事便是。”他顿了顿,目光隐晦扫过江绥苍白染血的脸,又添了一句,冰冷如霜,“官宦子弟,骄奢淫逸,仗势欺人者众。江家……不过冰山一角。”
每一个字,都像淬了冰的针,狠狠扎进江绥耳中。仗势欺人?骄奢淫逸?他看着自己洗得发白的袖口,看着母亲被踩在泥泞里的手,看着姨娘和姐姐们惊恐绝望的泪眼,一股冰冷的火焰猛地从心底窜起,烧得他五脏六腑都在剧痛!
“我父亲……不是!”他猛地挣扎抬头,不顾嘴角溢出的鲜血,吊梢眼里迸射出骇人的寒光,首刺陈修彦,“陈修彦!你大理寺办案,就是这般不分青红皂白,助纣为虐吗?!”
陈修彦眉头微不可察地一蹙,似乎没料到这看似文弱的少年竟有如此烈的反击。他并未动怒,只是眼神更冷了几分,带着一丝轻蔑:“江公子倒是伶牙俐齿。可惜,大理寺只认证据,不认口舌之利。”他不再看江绥,转向校尉,“带走。仔细搜查,片纸不得遗漏。”
“是!”校尉一挥手,兵丁粗暴地将江绥拖起。江绥不再挣扎,只是死死咬着牙,任由他们拖着,经过陈修彦身边时,他猛地侧过头,那双燃烧着恨意与不屈的吊梢眼,如同受伤的孤狼,狠狠剜了陈修彦一眼。
那一眼,深深刻进了陈修彦的眼底,入木三分却浑然不觉。
---
**三年后,西城陋巷**
寒风卷着破败门板上糊的旧年画,发出呜咽般的声响。逼仄的小院弥漫着一股浓重得化不开的药味。几间低矮的瓦房,窗户纸破了洞,用旧布勉强堵着。
江绥坐在冰冷的灶膛前的小杌子上,就着灶膛里最后一点微弱的余烬,借着破窗外透进的惨淡天光,小心翼翼地用一截快燃尽的蜡烛头,将一根细小的青蚨线穿入磨得光滑的骨针针孔。他指关节冻得发红,动作却稳而快。眉间那点小痣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黯淡。
“咳咳……咳咳咳……”剧烈的咳嗽声从里间传来,撕心裂肺,仿佛要将五脏六腑都咳出来。
江绥动作一滞,立刻放下针线,起身快步走进里屋。
窄小的土炕上,江母周氏蜷缩在打着补丁的薄被里,脸色蜡黄如金纸。她枯瘦的手紧紧攥着一方洗得发白、却浸满暗褐色血渍的帕子,每一次咳嗽都牵动着瘦弱的身体剧烈颤抖,如同风中残烛。
“娘……”江绥声音发紧,连忙坐到炕沿,扶起母亲,让她靠在自己单薄的肩上,另一只手力道适中地拍抚着她的背脊。那脊背嶙峋得硌手,隔着薄薄的衣衫,能清晰地摸到凸起的脊椎骨节。
林姨娘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汁进来,眼眶通红:“绥哥儿,药……快凉了。”
江绥接过粗瓷碗,试了试温度,小心地喂到母亲嘴边:“娘,喝点药吧。”
江母费力地睁开浑浊的眼,看着儿子年轻却写满疲惫与坚毅的脸,嘴唇翕动,想说什么,却被更猛烈的咳嗽淹没。黑褐色的药汁顺着她嘴角流下,混着新咳出的、刺目的鲜红血沫,染污了江绥靛青旧袍的前襟。
江绥的手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,随即更稳地扶住母亲,耐心地一点点喂着药,仿佛那刺目的红只是寻常污渍。他垂着眼睑,长长的睫毛掩盖了眼底翻涌的巨浪。
好不容易喂完药,江母靠在儿子怀里,气息微弱,枯瘦的手颤抖着摸索,抓住了江绥冰冷的手腕,声音气若游丝:“绥儿……你爹……是清白的……书院……束脩……”
“娘,您放心。”江绥的声音低沉却异常平稳,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,他反手握住母亲冰凉的手,“爹的清白,儿子定要讨回来。书院的束脩,儿子明日就去交。”
他目光扫过炕头一个打开的空木匣——那是大姐姐江蓉的嫁妆匣子,如今里面只剩下半匹褪色的红绸。江蓉坐在角落的矮凳上,抱着空匣子,无声地掉着眼泪,肩膀微微耸动。
“绥哥儿……”江蓉的声音几乎细不可闻,带着希冀和无助。
江绥望着她憔悴的面容,哪里还能看出来她如今不过双十年华,只不过一夕之间,家道中落,又惨遭夫家抛弃,如今更是沦为罪臣之女,未来几乎是一眼就望得到头。为了母亲的病,她变卖了不少体己和嫁妆,不过也依旧是杯水车薪。
全家的重担,一下就压在了江绥这个唯一的男丁身上。
江绥看着他,心中沉寂,泛着酸涩的涟漪,他喉结微动,嘴唇嗫嚅,却什么安慰的话也说不出口,只能伸出手安抚的拍了拍她的手臂。
窗外寒风呼啸,屋内是摇晃不定的昏黄烛光……
 书架
书架
 求书
求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