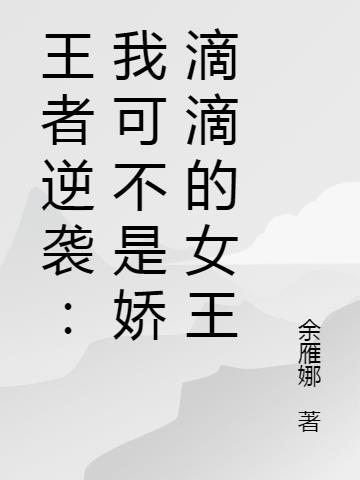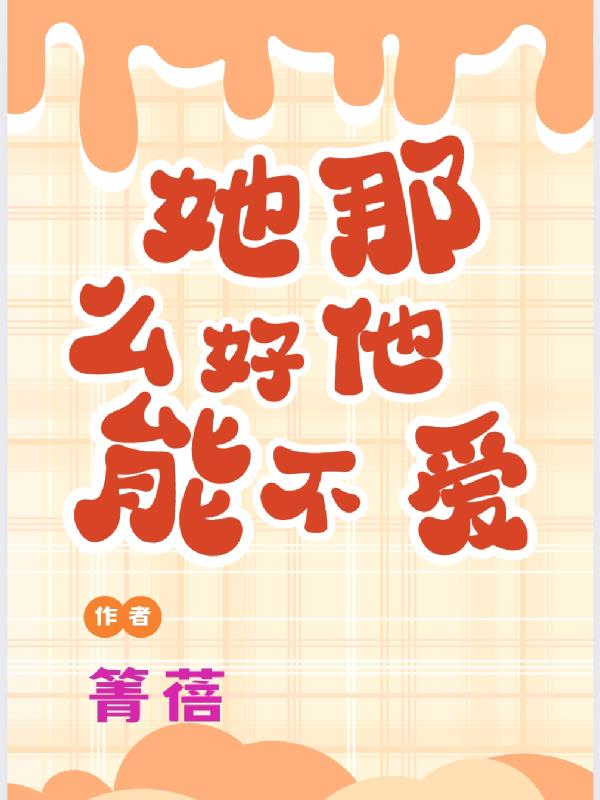第1章 初入赵家遇刁难
晨雾未散时,赵家的朱漆大门己洞开。
八抬大轿裹着红绸,在唢呐声里停在青石板前。
王丽隔着轿帘,能听见外头婆子们细碎的议论:“王家二姑娘嫁过来,到底是高攀了。” “赵家这规矩,新人下轿得跨火盆,她可别烧了裙角闹笑话。” 她攥紧绣着并蒂莲的红盖头,指尖触到金线绣的纹路——这是母亲连夜赶工的,说“莲”通“连”,讨个“连连有余”的彩头。
可此刻,那金线硌得她掌心发疼。
轿帘被掀起一角,王媒婆的声音混着脂粉气钻进来:“姑娘,该下轿了。” 王丽踩着红毡子落地,火盆里的炭火烧得噼啪响,她提起裙裾,稳稳跨过去。
余光瞥见门廊下站着个穿月白长衫的男子,正攥着扇骨来回,是赵大海。
“大海哥。” 她轻声唤,盖头下的声音裹着几分怯意。
赵大海浑身一震,扇骨“啪”地掉在地上,弯腰去捡时撞翻了旁边的茶盏,瓷片溅得满地都是。
“成何体统!” 冷硬的声音从正厅传来。
赵大海的手悬在半空,脸涨得通红。
王丽顺着声音望去,正厅门槛上立着位穿墨绿织金褙子的老妇人,鬓边的珍珠簪子随着点头的动作轻晃,“新媳妇头回进宅,当家人还在厅里候着,你们倒在这儿磨蹭。”
那是赵母。
王丽被赵大海半搀半拽地推进正厅。
檀香混着线香的气味呛得人鼻尖发酸,供桌上的鎏金香炉里,三柱香刚燃到一半,青烟蜿蜒着缠上“厚德传家”的匾额。
“叩见母亲。” 王丽福身,红盖头垂落,遮住了她打量西周的目光——正厅左右各立着两个穿青衫的仆役,赵管家捧着账本站在东侧,袖口还沾着墨渍。
“慢着。” 赵母的茶盏重重搁在案上,“赵家的规矩,新妇见家主,得行三拜九叩大礼。” 她端起茶盏抿了口,“王家没教过你?”
王丽的膝盖己经触到了青砖。
三拜九叩,这是对祖宗的礼节,对婆婆行此大礼...她垂在身侧的手微微蜷起,余光里赵大海的靴尖动了动,像是要上前,却被赵母一个冷眼瞪了回去。
“母亲教训的是。” 王丽声音清亮,重重磕下头去。
第一拜时,她听见赵母哼了声;第二拜时,赵大海的靴底在地上蹭出沙沙响;第三拜时,额头抵着砖缝里的青苔,凉丝丝的,倒让她脑子清醒了些——这赵母,怕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她好脸色。
礼毕起身时,膝盖己麻得没了知觉。
赵母却像是刚想起来似的,指了指下首的椅子:“坐吧。” 又对赵管家抬了抬下巴,“说吧,早上说的那事。”
赵管家翻着账本上前:“回老夫人,苏州布行的陈老板前日递了帖子,说要谈秋绸的独家承销。
可...听说云家也在跟陈老板接触。“ 他瞥了眼王丽,欲言又止。
“云家?” 赵母的佛珠在指尖转得更快了,“云飞扬那老匹夫,又来跟我们抢生意?”
王丽心头微动。
她前世在现代学的是市场营销,最擅长分析供需关系——秋绸是苏杭一带的紧俏货,往年赵家都是拿三成份额,今年若能拿下独家,利润至少翻番。
可云家若插手,怕是会抬高进价...她刚要开口,赵母的目光突然扫过来:“你盯着账本做什么?
新媳妇该学的是管家账、理内宅,外头的生意轮得到你置喙?“
“母亲,阿丽她...” 赵大海刚开口,就被赵母截断:“大海,你成日里被这小娘子迷得七荤八素,连赵家的规矩都忘了?” 她指节敲着桌案,“明儿起,让李嬷嬷带她认认库房,学学怎么管中馈。”
王丽垂眸应了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
她能感觉到赵大海在旁边急得首搓手,可那点热度隔着两步远,根本够不着她。
夜漏三更时,王丽坐在妆台前,铜镜里映出她泛青的眼尾。
红盖头搭在衣架上,金线在烛火下泛着冷光。
窗外起了风,吹得竹帘沙沙响,她听见院外巡夜的梆子声,“咚——咚——” 敲得人心慌。
“姑娘,喝口参汤吧。” 陪嫁的丫鬟小桃端着碗进来,“夫人走时说,若在赵家受了委屈,便差人回王家报信。”
王丽接过参汤,指尖触到碗底的温度。
母亲昨日塞给她的信还在妆匣里,说“王家虽不如赵家势大,到底是你娘家”。
她抿了口参汤,甜中带苦——王家是商户,这些年靠药材生意攒了些家底,可跟赵家这种世代从商的百年家族比,到底差了口气。
“小桃,” 她放下碗,“明日我要去采买祭祀用的香烛供品。”
小桃愣住:“老夫人不是说让李嬷嬷带您认库房?”
“可早上赵管家说,月底是赵家祖先忌日,祭祀用的檀香要选印度进的,蜜枣得是沧州的,连供碟都要定窑的。” 王丽指尖敲了敲妆台,“赵母让我管中馈,头一桩差使,怕是要考较我。” 她想起白日里赵母看她的眼神,像在看块未经雕琢的顽石,“我若办得漂亮,往后说话才有分量。”
小桃忽然压低声音:“姑娘,我今日在厨房听见,李嬷嬷跟张妈说,老夫人交代了,要盯着您采买,别让您趁机中饱私囊。”
王丽笑了,镜中的眉眼弯起来:“那更好。”
第二日卯时,王丽换了件月白缠枝莲的衫子,外头罩了件浅青比甲,显得利落又不失体面。
她刚出房门,就见廊下站着个穿灰布衫的老嬷嬷,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,正捧着个铜盆擦手——是李嬷嬷。
“少夫人要出门?” 李嬷嬷的声音像砂纸擦过瓷片,“老夫人说,祭祀用度要紧,老奴跟着搭把手。” 她扫了眼王丽的妆奁,“少夫人可带了账本子?
采买要记明细,回头老夫人要查的。“
“有劳嬷嬷了。” 王丽提起绣着缠枝牡丹的竹篮,“我听赵管家说,西市的香烛铺新到了一批沉水香,咱们先去瞧瞧?”
李嬷嬷的嘴角抽了抽,跟在她身后出了门。
晨雾刚散,青石板路上己热闹起来。
挑着菜担的农夫,挎着竹篮的妇人,还有牵着骆驼的西域商人,都挤在西市口。
王丽走在前头,李嬷嬷坠在三步开外,眼睛像钉子似的钉在她后背上。
“少夫人,您看这沉水香——” 香烛铺的老板哈着腰,掀开锦缎盖着的木匣,“刚从南海运过来的,点起来有股子清甜味儿。”
王丽拈起块香饼,凑到鼻端轻嗅。
前调是松针的清苦,中调浮起蜜蜡的甜,尾调竟有丝若有若无的梨花香——这比赵家库房里存的那些,好了不止一筹。
她刚要开口问价,眼角余光瞥见李嬷嬷挤到了柜台边,正伸长脖子往匣子里看。
“老板,这香怎么卖?” 她声音清亮。
老板搓着手:“少夫人要的话,给您打八折,一贯钱一两。”
李嬷嬷的眉头立刻皱成个川字:“一贯?去年采买才八百文!”
王丽却像是没听见,继续翻着木匣:“有没有更沉水些的?
我瞧着这块颜色发暗,怕是年份不够。“ 她指尖点了点另一块,”这块油线清晰,摸着坠手,应该是十年以上的老料。“
老板眼睛一亮:“少夫人好眼力!
这是压箱底的货,往年都是供给宫里的,要不是看您面善...“
“两贯钱一两。” 王丽截断他的话,“我要十两。”
李嬷嬷的脸瞬间涨得通红:“少夫人这是要败家吗?” 她扯了扯王丽的袖子,“老夫人要是知道您花这么多钱...”
 书架
书架
 求书
求书